夜半叩门的藏马熊:入户夺食、杀畜伤人,人熊冲突何解?
大河报·豫视频记者 梁奇慧
西藏那曲萨普神山的夜晚,户外博主林浩曾目睹多达36只藏马熊,最近时距离仅半米。游客与熊合影、投喂的画面在社交媒体刷屏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山脚下的羊秀乡,牧民们正忙着给门窗加装防护网与倒刺——这些高原猛兽已从昔日“远山的传说”,变成每日造访的“邻居”。

萨普神山的藏马熊(图片来源于网络)
在青海昆仑山腹地的无人区项目点,藏马熊更是夜夜光临的“常客”。田越和同事们常在深夜被熊破拆厨房门的声响惊醒,如今习以为常。在西藏那曲比如县白嘎乡,夜幕降临时,街道上游荡的藏马熊身影比比皆是。
随之而来的,是逐年升级的冲突:2014-2017年,三江源长江源区上报 296 起棕熊袭扰事件;2025年4月,西藏昌都一名青年牧民独自上山时,被刚结束冬眠的藏马熊咬伤致死。据大河报《看见》记者统计西藏“那曲公安”微信公众号的公开信息,截至2025年7月,当地警方在今年至少已处理了6起棕熊袭扰事件。
从无人区到乡镇街道,藏马熊正不断模糊着人与兽的活动边界。
当藏马熊闯入人类世界
田越驻扎在青海昆仑山腹地的一个无人区项目点,除了他和100多名同事,周遭便是各种野生动物,而几乎每晚必至的藏马熊是最显眼的“常客”。
熊的目标很明确,直奔垃圾堆和厨房,搜寻人类的食物和厨余垃圾。田越在宿舍里就能清晰听到熊撕扯厨房门窗的声响。成年藏马熊体重可达100到250公斤,“活动板房的门窗对它们而言如同玩具”。

被藏马熊入室的房屋(受访者供图)
鉴于熊的存在,田越和同事们被严令禁止天黑后外出,上厕所也须结伴,从最初的心惊胆战到如今的习以为常,田越已能透过宿舍窗户平静观察:最多时,可见四五只藏马熊在四五米远的垃圾堆上翻找。
熊的智商之高也超出田越的预料,它们能精准辨别无人居住的房屋,主动避开人类活动区域。最令人称奇的一幕是:藏马熊“像人一样”一手拎着厨余垃圾桶,直立行走着回到山上。“第二天早上,若做饭阿姨发现桶丢失,只需去半山坡寻回空桶即可。”

正在翻找垃圾的藏马熊(受访者供图)
在项目点工作的三年间,田越明显感觉“熊来得一年比一年多,以前是间隔一段时间才来,如今几乎每天都来”。据老同事回忆,早几年根本不见熊影,直到2020年才第一次碰见熊。
在广袤的无人区,似乎是人类闯入了熊的领地。然而在青藏地区的乡镇、城区街巷,藏马熊现身的频率也在与日俱增。
曾多次西藏自驾游的林浩对此也深有体会,在那曲比如县的白嘎乡,他就曾亲见“一到晚上,整个乡大街小巷都是熊”。他与同伴在饭店楼上吃饭,下楼就能与熊狭路相逢。当地居民有时打开门,门板竟会撞上门外的熊。“即便乡亲们也怕,但都习惯了,游客也习惯了。”

比如县一乡镇,翻找垃圾桶的藏马熊(图片来源于网络)
2024年6月,媒体曾报道,在白嘎乡一家酒店,两只棕熊一度被狗群围堵楼道里。酒店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称,山上熊很多,夜晚时分就会下山翻垃圾寻找食物,周边的熊一般不主动攻击人。
2025年7月,一位游客在那曲某民宿就餐时,一只藏马熊竟翻窗入室,堂而皇之到餐桌取食后扬长而去。
那曲地区羊秀乡的情形几乎与白嘎乡如出一辙。为防藏马熊入户,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门窗上加装了防护网、倒刺。
垃圾场:重塑熊生的“摄食天堂”
藏马熊,学名西藏棕熊,是棕熊的亚种,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其主要栖息于昆仑山、祁连山及喜马拉雅山之间高海拔的高山荒漠与高山草甸地带,是青藏高原上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。
西藏棕熊扮演着保护草原生态、控制家畜瘟疫扩散的重要益兽角色,被视为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中的伞护种(指保护该物种可同时保护同域其他物种的物种)和生境健康度的指示种(其生存状况反映整体环境质量),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意义重大。
尽管棕熊的原始栖息地环境严苛,人类通常难以接近,但眼下日益严峻的人熊冲突已不容忽视。青海省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创始人尹杭指出,整体来说,青藏高原地区多地都在发生人熊冲突。

雪境红外相机拍摄的藏马熊
那么,如今频发的人熊接触,是否源于熊数量泛滥?
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吴岚在一次分享中提到:1997年之前,青藏高原上西藏棕熊的种群密度为1-3只熊/平方公里。自2010年开始,她和团队对青藏高原一处14000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研究,发现有20-50只棕熊。由此可知,棕熊种群并没有明显增加。
尹杭亦表示,目前尚无确凿的研究数据证实棕熊种群增加,而想要统计棕熊数量本身亦非易事,因为棕熊的皮毛图案不像雪豹般具有唯一性,“我们曾花了很长时间去对一个垃圾场的熊进行观察,才能大概分辨出20只熊”。
追根溯源,伴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定居工程的推进,牧民开始定期储存大量的食物,其中“肉房(牧民储肉专用房)堪称熊的最爱”,酥油、炒青稞粉等热量高的食物,也颇受熊的欢迎。
更关键的问题是,当牧民们从游牧走向定居,固定堆放垃圾的场地也在随之增多,原本在野外艰难“刨食儿”的熊们逐渐将垃圾场当作获取食物的“大食堂”。

垃圾场里的藏马熊(雪境供图)
至此, 看似毫不相干的棕熊与垃圾, 因人类活动而紧密相连。
2024年,雪境团队实地调查了高原地区的10个县城及若干人口密集的乡镇垃圾填埋场,发现那些混杂大量厨余的垃圾场,最受包括棕熊在内的野生动物“追捧”。
几只熊崽在垃圾场内翻找,爪子不时触碰碎酒瓶、废铜烂铁,发出刺耳的撞击声。周围还不时地响起犬吠和其他不明动物的嚎叫,这一晚,雪境团队的成员目睹20多只棕熊在此徘徊觅食,其中不乏带着幼崽的母熊。“幼崽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学习在高原雪地追猎,而是专注于翻找人类的废弃物”——垃圾正“重塑”野生动物的生活方式。
“熊的生存本能就是追逐热量,足够的热量保障其繁衍。”北京草原之盟环境保护促进中心负责人张晓磊如是说。
野外生存的西藏棕熊主要以旱獭、鼠兔、岩羊及植物为食,兼具主动捕食与食腐习性。在青藏高原,它无疑是食物链顶端的存在,但更是精明的机会主义杂食者。“如果躺在垃圾场里就能轻松获取足够的食物,它何须大费周章地去挖掘半个篮球场的面积去捕食旱獭?”尹杭指出。
吴岚博士曾在分享中量化比较:无论是“偷盗”的面粉酥油,还是风干牛肉,都比吃一只旱獭获得能量要大得多,利益代价比基本在70倍以上。
边界模糊的后果:入室、捕食牲畜、伤人
熊爱上人类的食物,直接导致人熊接触频密,进而引发愈演愈烈的冲突。
据红星新闻报道,2014-2017年,仅在三江源的长江源区,就上报296起棕熊袭扰案件,其中入室造成财产损失占九成,达到93.58%,捕食牲畜占4.73%,伤人占1.69%。同期,据青海省林草局报告,有9位牧民受到棕熊攻击后身亡。
据不完全统计,2020年5月到8月期间,青海治多县、囊谦县和格尔木市先后有7人遭遇棕熊袭击,其中2人死亡,5人受伤。
大河报《看见》记者对西藏“那曲公安”微信公众号的公开信息进行初步统计,截至2025年7月,当地警方至少已处理了6起棕熊袭扰事件,包括棕熊入室、袭击牲畜、伤人等。

2025年西藏那曲地区双湖县,村民在放羊途中毫无征兆地遭到棕熊袭击导致手部受伤(图片来源:那曲公安微信公众号)
2025年4月,西藏昌都达升乡一位青年牧民骑摩托车独自上山采鹿角时,被棕熊咬伤致死。
张晓磊告诉大河报《看见》记者,据他分析,这位青年是在落单的情况下上了山,同时,4月是棕熊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时节,正是极度饥饿的时候。他补充道,母熊揣着崽儿的时候,也会增加攻击性。
尹杭也依据经验给出防熊建议:野外活动时,6人以上结伴同行基本不会被熊袭击,此外最好带狗,“狗比人敏锐,会提前警示”。
雪境团队持续在高原地区协助牧民防熊,青海省囊谦县东坝乡即为其帮扶的试点社区之一。在当地政府、环保组织的支持下,雪境已经为东坝乡的43户牧民安装了电围栏,这种非致命性装置既能有效阻熊于门外, 又不对其或人造成伤害。

雪境、当地环保协会和当地牧民一起安装的电围栏(图片来源于雪境)
尹杭介绍,这些成本约5000元的电围栏效果显著。今年,东坝乡有十几户牧民选择自费加装。此外,在储存食物的房屋附近每10天喷一次大蒜水,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驱熊手段。
2022年5月,《青海省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保险赔偿试点方案》正式实施,该方案在明确赔偿范围、优化理赔流程的同时,大幅提升了赔付标准:人员死亡赔偿标准提高至60万元,较10年前标准提高近三倍。
共存之路各守边界:需扭转人熊亲密的误区
现实中人熊边界日益模糊,社交媒体上对棕熊的关注度亦居高不下。
在许多户外博主、游客看来,藏马熊是“憨态可掬”的“高原大仓鼠”,拍合照或者投喂在国道边等待的藏马熊几乎成了在川西、青海、西藏等地自驾游的“打卡”项目。此类内容上传至社交平台,动辄收获上万点赞。

游客们正在拍摄藏马熊(受访者供图)
2024年8月,户外博主林浩曾在西藏萨普神山上多次近距离与藏马熊接触,最近的时候,距离只有半米不到。他告诉大河报《看见》记者,他曾在萨普神山上多次直播藏马熊,“当时我每天追着熊跑,最多一晚上见过36只藏马熊。”
多次在西藏自驾游的林浩并不畏惧藏马熊,更多的是抱以同情,但他在采访中多次告诉记者,“大家还是要远离藏马熊,毕竟这是野生动物”。
2025年6月,一位博主在萨普神山与熊近距离合影的图片被上传到社交媒体后,评论区许多网友直言这是错误的行为,有人提醒“拍这些是个人的自由,但不要让大众认为这是一件安全的事情”。
此外,网上还流传着诸如藏马熊“会扮演成人,招手引诱人类过去并吃掉”的传言。“或许这些传言与牧区流传的熊传说有关。”尹杭坦言,人并不在棕熊的食谱内,但如果有朝一日,习惯了与人接触的棕熊不再惧怕人类,并开始尝试将人类当作食物,那么带来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。“人熊接触频率越高,发生伤人、吃人事件的概率就越高,这正是我们必须竭力避免的。”
《博物》杂志曾撰文澄清:历史记载中造成人类连环死亡的“食人熊”案例并不常见,这些个体大都因伤病失去了捕食能力,最终将目光转向了更易捕食的人类。上述传言虽无科学依据,但棕熊的危险性是真实存在的。任何试图将其“萌化”而忽视其危险性的宣传,某种程度上是致命的。

西藏昌都当堆乡,在垃圾场翻找的藏马熊(受访者供图)
作为长期关注野生动物保护及人兽冲突的研究者,尹杭与雪境团队并不希望棕熊被妖魔化而遭憎恨。同时,他们也指出,大量进食人类精加工食物,对熊自身健康与寿命同样构成风险。
想要扭转过于亲密的人熊关系,显然需从根源——改变熊的取食习惯入手,高原垃圾处理也亟待更系统化的调整。
雪境团队发现,青海玉树州的垃圾处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当地自从2022年起推行“全域无垃圾”政策,撤离大量公共垃圾点,垃圾收集后被直接运到填埋场,由相关部门统一管理。这些曾被熊频繁“光顾”的垃圾点关停后,熊自然便退去了。
即便如此,要让已习惯“躺平式”取食的棕熊重归野外生活,仍是一条漫漫长路。尹杭援引美国黄石公园的案例:该地也曾出现熊依赖垃圾填埋场觅食的现象,垃圾填埋场虽然逐渐关停,但直到40多年后,熊才彻底回到野外,重启自然捕食模式。
让人类的生活重归安全宁静,让熊重返荒野自由生存,不再被垃圾“圈养”,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,划定清晰的人熊边界,“人熊共存,不是共居一地,而是各守疆域——你在高原觅食,我在村庄生活,遥遥相望,互不打扰”。(文中田越、林浩均为化名)(新闻报料请私信微信公众号“大河看见”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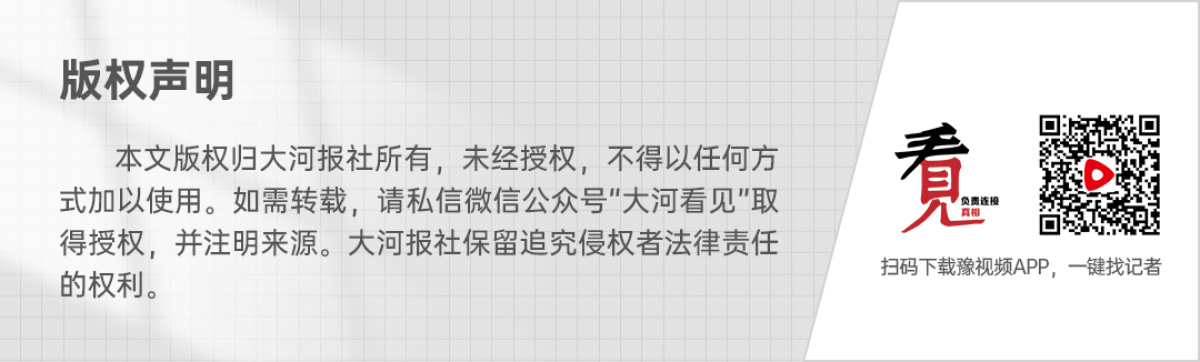
来源:大河报·豫视频 编辑:刘惠杰
